历史重演:赫鲁晓夫“逼宫”与“被逼宫” >> 阅读
历史重演:赫鲁晓夫“逼宫”与“被逼宫”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每个独裁者到晚年无不殚精竭虑地考虑接班人问题。往大处说,这是革命的千秋大业是否后继有人;往小处说,也涉及自己死后的身家性命功过荣辱。
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好不容易选中的接班人,却层出不穷地变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谢尔盖回忆说:“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定不下来。他想找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赫鲁晓夫最初选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科兹洛夫曾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更为重要的,科兹洛夫与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实力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内政路线的代表者。自赫鲁晓夫粉碎“马、卡、莫反党集团”后,科兹洛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成为苏联党的二把手。
然而,1963年科兹洛夫突然中风,当赫鲁晓夫赶到医院望着瘫在病床上的科兹洛夫时,说了一句至今想来也有点让人莫明其妙的话:“科兹洛夫在装病,该打起精神来去上班了。”这里,赫鲁晓夫流露出的是怎样一种情感?是一种“窃喜”,还是一种“遗憾”?科兹洛夫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没能再站起来。到赫鲁晓夫垮台中央委员会重新改组前,他虽仍保留着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职务,但实际上已是个“职务(植物)人”。
“早夭”对科兹洛夫而言,幸抑或不幸?如果没有这一变故,他就能顺利接班?在苏维埃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接班人能顺顺当当地继位。二把手是一个高危位置。比如在十月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托洛茨基,他的肖像曾同列宁并排挂,被看做列宁的当然接班人,可他却死在斯大林派去的刺客手里;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大力神”的布哈林,曾是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排名更靠前的人物,在19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遭到枪决;名声曾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斯大林的基洛夫也死于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刺杀案。(对这一谋杀案的审讯,斯大林又一箭双雕地处决了潜在的威胁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二战后曾处于二把手位置的日丹诺夫,也不明不白地死于“医生谋杀案”;而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马林科夫等无一不落入“反党集团”的悲惨命运。
此后,赫鲁晓夫为接班人选绞尽了脑汁。这个接班人,一定要选一个年纪轻的人。用赫鲁晓夫的话说,现在主席团的人都是“爷爷辈”的人,人到了60岁就不想将来的事了,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这个接班人,既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国防,还要懂得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得“靠得住”。
赫鲁晓夫把目光投向谢列平。谢列平几个条件都还符合:共青团出身,担任过多年共青团的第一书记,有作为一把手的领导经验;他是现任主席团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对中央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熟悉。但不足的是,他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于是赫鲁晓夫提议,让谢列平到列宁格勒去当一段州委书记,那里有全苏联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经过这样的地方锻炼,就可以回中央任要职了。可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谢列平拒绝这项任命——他认为这是降职,是赫鲁晓夫在找借口排挤自己。谢列平的表现,使赫鲁晓夫猛然意识到:原来谢列平并没把自己当成赫鲁晓夫的人。
后来,赫鲁晓夫还想到过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精明能干,经验丰富,又懂经济,也能谦和与人共事。但赫鲁晓夫又觉得他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交给他分管的工作始终处理得不理想。
再后来,赫鲁晓夫还曾考虑过勃列日涅夫——他论经验论资历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但赫鲁晓夫又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自己情绪的左右”。战前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某州的党委书记时,当地人送他一个绰号“芭蕾舞女演员”,说他总像个陀螺一样旋转不停,像契诃夫笔下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这样的人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当然不行了。
也许是作为一种“考察”,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时放在了书记处,把权力分给两个“第二书记”,其中大概有着中国典故“二桃杀三士”的意味。赫鲁晓夫显然向斯大林学到了重要的政治权术。
赫鲁晓夫还有过其他种种考虑。正是这一次次的选择与放弃,使每个进入赫鲁晓夫视线的人饱受跌宕起伏的折磨。当年克里姆林宫里流传一句话:“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用“接班人”的标准审视,任何缺点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正是这样,他把一个个原本的盟友,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亲手制造了1964年那场“宫廷政变”的基础。
回顾赫鲁晓夫选择接班人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历史性思索。这大概也是民主选举和“御赐钦定”的天壤之别吧。
告别政坛的“绝唱”
其实,“宫廷政变”之前,赫鲁晓夫并非浑然不觉。谢尔盖从伊格纳托夫的卫队长那儿得到情报,告诉了父亲:
父亲陷入了沉思。
“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伊格纳托夫倒有可能,他很不满意,而且这个人本来就不好。可是他同其他人会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父亲继续着昨天的话题,他开门见山地说:“看来你说的那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来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昨天你讲的话说了一遍,波德戈尔内把我挖苦了一通。‘亏你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
赫鲁晓夫的轻信和波德戈尔内的狡诈,又构成了一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故事。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若不信,随着各方面情报的汇聚,事情变得有鼻子有眼,一场阴谋显然正在酝酿中;可若相信,赫鲁晓夫的精神面临崩溃:因为发难反对他的人竟如此众多,几乎所有的昔日拥戴者都成了反对派。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上粉碎第一次宫廷政变后提拔上来的。不信任他们,在苏联还能信任谁?
即便危机已经来临,赫鲁晓夫从度假地被召回克里姆林宫时,他还对米高扬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真要让我交权,我也不准备做任何反抗。”
在最后签署“退休声明”前,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他说:“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这篇告别政坛的“绝唱”是发人深省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它的功劳,党的功劳。我和你们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斗争的……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从来没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你们指控我同时兼任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不过容我客观地讲,我本人并没有力争这样的兼任。回想一下吧,问题是集体决定的,而且我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坚持让我兼任嘛。也许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决定,可是你们全都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这样做。现在你们却指控我兼任两个职务了。
当时,所有的反对派都不敢相信,赫鲁晓夫这种个性的人面对“逼宫”会逆来顺受善罢甘休。原以为他一定会有什么意外之举,然而没有。
赫鲁晓夫终究以独特的告别政坛的“绝唱”,谱写了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他以自身权力场的沉浮,完成了一个领袖人物从神到人的回归。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关东大地震后谣言纷起让日当局恐慌
- 下一篇:柏林墙野兔:见证自由的没落与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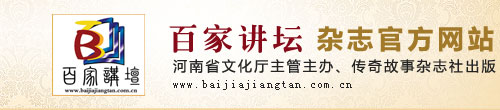
 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